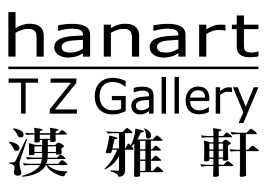BOLOHO: 接活,接着活下去
評論文章
來自中國廣州的藝術團體菠蘿核(BOLOHO),在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打造了一間「工廠食堂」。觀眾們可以在這裡一邊享用亞洲菜餚,一邊觀看電視屏幕上由BOLOHO創作的系列情景喜劇BOLOHOPE。他們所在的Hübner Areal展區原是卡塞爾東部的一座工廠,此番空間中的牆紙和桌布上鋪滿文字宣言和可愛圖案,幾扇屏風以照料和縫紉為主題——正是以”共同勞作”為實踐中心的BOLOHO,在輕鬆幽默的態度中回應了當代藝術所面臨的矛盾機制。
本期推送中,我們對話了正在卡塞爾的菠蘿核(BOLOHO),詳細介紹他們基於友誼的運作分配模式,如何在互助中去確認自己的勞動價值,以及本次參展作品BOLOHOPE的創作始末,並分享了未來與文獻展「閱覽室」合作的更多出版計劃。
卷宗書店:請談談你們緣何決定建立這個自我組織!
菠蘿核:BOLOHO是菠蘿核的諧音,是大樹菠蘿的種子。習慣了食用果肉而將菠蘿核扔掉的人們,常常不知道或忘記了它也是一道別具風味的美食。BOLOHO一開始是BUBU(劉嘉雯)與CAT(黃婉珊)兩個家庭職業女性的創業計劃,也是在家之外的一處透氣的地方,在這裡希望能把生活和工作的頭緒理一理。經過這幾年的時間,其他成員陸續加入,例如朱建林、李致恿、馮偉敬。而後,創業的部分逐漸形成了一個」公司”平台,在給無法只靠藝術謀生的大家”接單”的同時,也給大家提供了去思考、辨析和解決一些現實問題的契機。
菠蘿核:其實自2010年起,當BOLOHO主要成員們還是學生時,就開始陸續發起了一些自組織的集體項目。在十多年間,大家各自參與了種種形態的集體實踐與項目,也經歷了不同性質的職業和工作。這些經驗使我們體認到各種機制的失靈(從學校、機構到城市與社會層面)對創作者的生存和發展帶來的具體影響。或許,BOLOHO也是我們漫長集體實踐歷程中的一次新的行動。在個體支持體系和可持續發展框架極度匱乏的現狀下,我們想嘗試主動地與各種社會資源交往和對話,同時又不被完全捲入到任何機制的現有邏輯中,以此來探索一點其他選擇的空間。
卷宗書店:在廣州,菠蘿核的實體空間場所是固定的嗎,是否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經歷過變遷?
菠蘿核:BOLOHO的空間位於一個廣州老城區的居民樓中,生活交通也挺方便的,周圍都是老房子。外地過來的朋友也常驚訝於菠蘿核附近房子跟其他一線城市相比,租金的性價比之高。興許「城市建設」的龐大機器也不是無所不能的,也有它力所不逮的地帶?廣州老城區土地的複雜構成作為一種掩護,讓我們有了相對固定的空間。
卷宗書店:成員在平時線下的聚會頻率如何?會開展哪些活動?對你們來說,共同勞作是最重要的嗎?
菠蘿核:我們幾乎每天都會見面,一起工作,做做飯、種種菜和帶孩子。共同勞作對BOLOHO的狀態而言,似乎不是需要特別去發起和安排的”事件”,而是隨時都在發生著的日常對話。例如,BOLOHO作為一個空間,大家對它的維護是在不同的時間,以各自的習慣和愛好去共同付出的:你經常會發現客廳多了新作的二手物料的盆景插花,或是撿來修好的”新”傢具,陽台又多種了一盆番茄,牆上可能會多出幾張手稿,等等。
菠蘿核:我們也更注重”共同勞作”中身體經驗和情感緯度。比如,平時工作的兩餐是大家工作後所必需的營養補充和身體需求。除了食物本身,一起烹飪和用餐逐漸成為了BOLOHO成員們去理解彼此和建構信任的重要時刻。
我們在此基礎上發起的”永遠十八廚房”(Forever 18 Kitchen),邀請長輩們、朋友們不定期地來主理或即興參與,這些通過食物所分享的記憶、知識,以及彼此的具身感受,拉近了不同代際和不同價值之間的距離,也充實了在異鄉生活和相處的意義。
菠蘿核:可能相較於”共同勞作”這個概念,我們更願意去思考和探索什麼是我們的”共同需要”,什麼樣的”基建”才能夠為可持續的共處與協作提供支持?
在BOLOHO,”基建”本身不只是空間性的,比如一起承擔維繫這個空間和平台所需的資金、成本與勞動等;它也很強調時間性,在更穩定的集體生活敘事中實現持續的自我認知。它促使著我們盡可能去真實地理解自身和彼此的基本生活所需為何,以及各自對同一項目或事件的理解處於怎樣的狀態和感覺,在此基礎上盡量平衡節奏和彼此接近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困難
的事情,而不是完全地依靠和輕信一套看似公道的程序以其結論。在我們的經驗中,在組織內部消除了層級和權威的平等程序,也可能因為忽略了人們在資源、能力和狀態上的差異,而導致新的集中,它更為隱蔽,也更為”正確”,卻激發著集體內在的焦慮與競爭。
卷宗書店:在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上將”工廠食堂”作為展廳,這個空間是如何選擇和佈置的?
菠蘿核:應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之邀,BOLOHO發起了《BOLOHOPE》項目,其中包括了迷你情景喜劇,繪畫與縫紉,創意文本及空間裝置設計等集體的創作與實踐。在情景喜劇的部分,《BOLOHOPE》的故事本身是圍繞著一個開餐廳的計劃來推進的。因此,策展團隊也呼應了我們的提議,將Hübner Areal 展區的「工廠食堂」提供給我們作為整個項目的「展廳」,並為我們推薦了當地有經驗的中餐館來運營它,為展覽期間的到訪者提供一個休憩和用餐的空間。
菠蘿核:與糅合了現實與想象的《BOLOHOPE》劇情一樣,餐廳與展廳的重疊,也折射著我們想與人們分享的那些多重的經驗與記憶。BOLOHO成員有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選擇以情景劇作為創作框架,跟我們小時候都有與家人一邊吃飯一邊收看港台電視的經驗有關,那是我們曾經瞭解世界的一個窗口。也許,當年在小小的屏幕里耳濡目染的幽默,正是表達我們時下苦樂的最自然和最熟悉的方式。劇中會出現一些港台電視劇的經典橋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迎客松」畫面;我們主題曲的前奏是TVB新聞節目的音樂和六合彩的背景聲。同時,我們用集體繪畫和縫紉創作的屏風將整個餐廳劃分成了四個用餐(影像)的空間,依照故事線索每個空間播放一集情景劇。
菠蘿核:在《BOLOHOPE》劇集的每一集劇情中,都插播了四個菠蘿核與閱覽室(李筱天、劉菂、謝思堰主持)合作製作的「廣告」。這些廣告採集了我們不同朋友們的句子,我們為這些句子設計了一個看似商業品牌的logo,並與菠蘿核平時即興記錄和創作的影像片段呼應呈現。這些句子與logo也應用到展覽現場空間的牆壁與桌面上。
菠蘿核:在創作《BOLOHOPE》的一整年里,我們所面臨的整個環境在激烈的變化,不管是我們生活的周遭還是世界的各地,不安與不確定感日益增長,也許HOPE這個詞語已被宣傳濫用,但在我們而言,HOPE是在種種日常生活的災難性現場中,我們試著用集體性的創作去窺測那些可以掙脫各種系統與體制裹挾的機會,去描述那些從未停止折磨著我們的慾望、困境與願景。來到文獻展的觀眾們,將在Hübner Areal一樓的餐廳中目睹菠蘿核大家庭的一次集體逃逸。它也極有可能是我們又一次」失敗」的行動和嘗試。
卷宗書店:根據你們的觀察,現場觀眾是如何反應的?BOLOHO收到了哪些反饋呢?
菠蘿核:這個餐廳是個放鬆休閒同時也可以辦公的地方。除了前來就餐的人,其他觀眾也可以在這裡小憩,約人見面,或者坐下來使用電腦,還有一批批暑假期間從全球趕來觀摩文獻展的學生群體在這裡開展小組討論。而BOLOHO的情景劇就提供了這樣一個輕鬆愉快的背景環境。世界各地的觀眾都是比較自在地在使用這個空間。與此同時,我們也會在展覽期間用餐廳舉行不同主題的活動。
之前我們也擔心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能不能理解情景劇裡面的梗,但我們目前所收到的反饋都是比較積極和鼓勵的,有一些特別契合BOLOHO的笑點節奏或者美學風格的朋友笑的格外開心。還有其他參展藝術家告訴我們,他們想念這個餐廳了,要帶不同的朋友回去繼續吃。和菠蘿核同一個迷你小組(mini majelis)的柬埔寨藝術家Khvay Samnang,他已經參加過了上一屆文獻展,這屆和Sa Sa Art Project 一起參展,和我們在同一個展場。他和家人在開幕前兩周就已經到達卡塞爾,布展期間時常跑上樓去看我們的展布得怎麼樣了,我們還沒到的時候他就拍了很多照片,直到最後所有繪畫屏風、影像和桌布都擺放完畢,開幕見面時他才告訴我們,你們的作品真的很棒,我們很感念這些鼓勵。當然,可能也有不喜歡或者持批評意見的人,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
卷宗書店:作為一個基於友誼的經濟實體,菠蘿核的勞動分工及分配方式是如何約定的?
菠蘿核:BOLOHO一開始就希望通過接活來自給自足,我們的經濟來源主要是設計,策劃,藝術製作之類的項目收入。我們是以按勞分配的方式和參與者合作的。在我們接到一個單的時候,我們會發起一個項目,邀請不同能力的朋友參與,製作一個分配表,表格里會按不同的工種做一個大致的預分配。其中裡面有一部分比例(20%)我們會投入在「基建」,即用以維持菠蘿核空間正常運作的租金、稅務及維護成本。在最後的項目結束後會根據實際情況做調整,每個項目參與者會給出自己的分配比例,通過參與者一同商討得到最終結果。
◉關於分工及分配方式的手稿
卷宗書店:在當下日趨原子化與物理隔離加劇的社會中,彼此信任、團結工作的藝術創作集體(collective)越來越難?可否舉例說明你們如何應對外在的隔閡壓力?
菠蘿核:對於「當下日趨原子化與物理隔離加劇」,每一個人都感同身受。但相比「外在的隔閡壓力」,我們可能更在意如何能「彼此信任、團結工作」。BOLOHO的日常決策是由5位成員共同商討的,卻也比較鬆散,很多時候每個人要負責和面對不同的事務,遇到需要立刻決策的情況,可以與協同工作的相應夥伴溝通,甚至負責此事的成員個人也可以迅速做決定,沒有特別要走的「程序」。例如,情景劇在籌備時其實有兩個名字備選,一個是bolohope,一個是boloho_lol。給出boloho_lol建議的朋友說,我們的劇是一部喜劇,lol是笑的意思,更可愛一些。兩個名字大家都很喜歡,於是就決定讓鯉魚(CAT與李致恿的孩子)選,鯉魚選了bolohope,所以就這麼定了,而boloho_lol被用作了我們Instagram帳號的名字。
菠蘿核:這種非程序的信任與默契,成為了我們協同工作的重要基礎,它有時候可以跳過很多不必要的步驟,讓決策的程序更靈活,也讓項目更容易被推進。當然,「信任」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和輕鬆,但其實我們成員都是認識多年、經歷過不同集體/團體的實踐的老朋友,磨合得比較徹底。
另外,我們也的確希望做決定的時候能夠相對簡單和輕鬆,一來是我們比較在意時間的效率,希望可以盡快完成工作給大家留出更多自由的時間;第二是我們強調共同承擔所有決定的後果。尤其是當事情出現「意外/問題/錯漏」時,正是最需要團結和協作的時刻,只讓做出決策的人承擔後果是過於沈重的。每當這個時候,我們也會召集所有的成員一起開會趕工,來溝通善後,但處理的原則是:大家協商一致,共同決定,共同承擔。
在組織結構上,我們沒有「領導」,沒有層級,每位成員都是平等的,照料彼此是我們最珍視的練習,雖然沒那麼簡單輕鬆,重要是要把自己感受不適的部分說出來,彼此分擔。因此我們所理解的集體,不是一種和「個人主義」相對立的東西,不是講求「投票」、「議程」的團體,而是一種可以允許個人探索自我、包容彼此並共同承擔的友愛空間。
卷宗書店:針對屬於自己的創作,和作為外包而完成的「接活」,會有不同的風格清晰區分嗎?
菠蘿核: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接活,就是接著活下去。」接活對於我們而言,一方面是維繫大家生活基本所需的主要經濟來源,另一方面接活的過程也是我們創作的田野。我們在藝術創作的很多辦法可以應用到接活上,同樣,接活的很多經驗也可以轉化到創作表達中。例如,這次《BOLOHOPE》的劇情中很多情節都是來自接活中的經歷,而接活過程中積累的不同技能(例如平面設計、影像、動畫)也充實了我們的創作語言。也許,一開始接活的確更多是我們應對資源和分配問題的生存策略。但過程中,它也逐漸打破了許多那種封閉的藝術家式的自我想象,在與種種具體問題的辨析與周旋中,賦予了創作者主體新的視角和流動性。至於風格,我們在接活或創作上都不是最在意的,我們更在意生產過程人與人的交往,不管是甲方與乙方還是策展人與藝術家,發展真實而彼此尊重的關係是我們實踐中最為投入的。
卷宗書店:本屆文獻展與「閱覽室」合作的出版計劃,可以具體和我們談一下會有哪些出版物嗎?作為「最不以物為本」的一屆文獻展,實體書對你們來說是什麼角色呢?「閱覽室」也包括視頻、縫紉、烹飪等形式嗎?
菠蘿核:與本屆文獻展有關的出版計劃,除了已經編譯完畢的《米倉》小冊子,閱覽室還有一個和菠蘿核所在的「迷你小組」(mini majelis)合作的出版物,內容為來自各成員家鄉(孟買,台灣,柬埔寨,廣東等地)的食譜,目前正在製作中。此外,閱覽室也將和亞洲藝術文獻庫開展一些共同出版項目,記錄本屆文獻展的內容。實體書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個物件,一個媒介,一個熟悉的對話者,更是一份歷史的見證。
菠蘿核:《米倉》中文版的編輯工作主要是於今年2月至5月進行的。當時劉菂在香港,謝思堰在深圳,李筱天在廣州。然而香港從今年2月起,深圳從3月,廣州從4月起,陸續開始出現與疫情相關的不同程度的封控。因此,這個編輯的過程進行地較緩慢,也是我們互相吐嘈互相提供情感支持的過程。自《米倉》英文版小冊子於2020年2月完成後,糟糕的新聞一件接一件,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做為譯者和編者的我們,在認真讀了米倉的故事和願景之後,感到很唏噓。那是一個關於這個世界曾經擁有過,或者至少本來可以擁有的更好的可能的故事。
卷宗書店:除了內部的互相支撐,菠蘿核如何「向外」去踐行「公共性」?換句話說,你們具體如何理解公共性?在獲得文獻展種子基金後,可以談談未來將如何使用這筆經費嗎?
菠蘿核:與單一個體與公共性內外之分的區別略有不同,BOLOHO本身是一個協作集體,在相互照料和相互支撐的過程中,需要我們不斷去辨析彼此的需要和關切,持續地去建構和修復集體之間的信任和基建。它本身就考驗著我們對自我、他者等公共性關鍵的概念,以及對其基礎價值與關係的理解力和行動力。這些所謂”內部”的日常練習,是幫助我們每一個成員去理解和體認”公共性”具體為何的重要過程。對於我們來說,公共性並非只是抽象的概念和律令,而是需要各自在日常中具體展開的共同想象與敘事。
菠蘿核:此次文獻展的種子基金,正是將”藝術家費”這一刻板的概念轉變成一種充滿想象的敘事。我們理解種子基金的提法是嘗試將創作者從”藝術家”的身份桎梏中釋放,使大家獲得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這背後的基礎依舊是某種對信任的理解。這筆費用已經融入到我們與米倉近一年的項目合作和未來可能的協作之中。我們期待著在此次文獻展工作框架與米倉網絡資源的支持下,在更廣闊的公共性領域去學習與練習,更多具體的工作還有待時間來慢慢展開。
卷宗書店:菠蘿核廣州空間的書架,也是你們共同佈置的嗎?可以從中選出三本能夠代表你們的書,推薦給卷宗書店的讀者嗎?
《別殺我,我還在愛!——向黃小鵬致敬》, 2021
《馮火月刊》 109 期,2022
《米倉》,2022